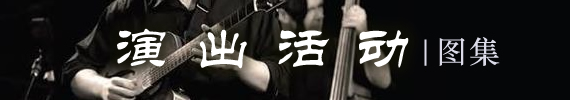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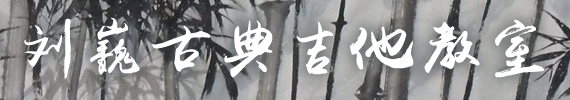
|
明明十二平均律由中国明代朱载堉最早精确计算发明,现代音乐理论却由西方构建?这背后藏着一场跨越东西方的音乐接力——中国埋下精密律制的种子,西方却用五线谱、和声学与调性体系浇灌出参天大树。
当十二平均律遇见西方音乐思维,一场关于音乐宇宙的规则重塑就此展开,答案就藏在音符与历史的交织里。
1610年(万历三十八年)5月初,夜已深,西斜的新月向北京城洒下眷恋的眼神。
北京西城区一所宅子里还点着灯,一个老外支撑着颤抖的双手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。
月落乌啼,油尽灯枯。在天朝上国辗转传教30年后,他带着一份还算优异的成绩单去向上帝述职了。
这个老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利玛窦。
老窦的同事将日记带回去后整理出版,洋人们给它取了个野心勃勃的名字——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。
在这本书的取名上,他们不仅充满侵略的野心,而且同样鸡贼异常,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汉译版书名叫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。
当时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,西方国家对外扩张,劫掠世界的态势已经形成,从书名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来看,这些老牌帝国主义想要侵略、征服天朝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。
当时的大明王朝GDP占全球的55%,是当仁不让的超级帝国,总以为西方是夜郎自大而已,直到乾隆年间,对此依旧傲慢狂傲。
《利玛窦札记》详细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和成果,同时记录了老窦同志这些年在天朝上国的所见所闻、科技文化,他成了当时欧洲了解华夏的镜子。
更要紧的是,这本书中记录了朱载堉领先世界的重大发明——十二平均律。这一重大发明,在欧洲开枝散叶,繁荣发展,形成了现代音乐理论的基础。
300年后,列强们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国门,胡适、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从西方学习了回来,不过已经没多少人知道它其实源自华夏了。
1581年的利玛窦大部分时间在马六甲通往澳门的船上漂着。
一年前他满怀荣耀与期待走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,怀揣着教皇的敕令与激情踏上去东方帝国传教的快船,向大明帝国驶来。
当时虽然麦哲伦的船队已经绕地球一周,但从欧洲远洋至东亚还是非常困难的,利玛窦在途中就身染重病,差点挂掉,这一年他29周岁。
不过,在这一年,45岁的朱载堉出版了著作《律历融通》,在该书的序言中,他提到一个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,并简述了该成果的重要性和计算的结果。
有意思的是,这一年伽利略他老爸也在研究这件事,不过最终一无所获。
1583年9月10日,利玛窦心潮澎湃满面春风。
这天他终于踏足心心念念的大明土地,准备开始实现在东方传播天主教的事业。
几个月后朱载堉出版了新书《律学新说》。
在我们之前发过的文章《中国最有才的富二代》中说了,朱载堉之所以出版这本新书,是因为《律历融通》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。
万历的亲堂叔,出版新书后竟然没有热搜没上头条,哪怕娱乐新闻都对此只字不提,眼看一生的心血要付诸东流,朱公子不甘心。
于是在新书《律学新说》中,他详细阐述了3年前在《律历融通》的序言中提到的研究成果,并陈述了详细的计算过程。
计算过程的第一步是对2开方,但是当时中西方的数学里是没有开方运算的,也就是说是朱载堉率先进行了开方运算,这是朱公子对数学界的贡献。
有意思的是,2000多年前,毕达哥拉斯在探索数字奥秘的过程中,也发现了声音的本质就是物体振动时产生的,并通过“五度相生律”也发现了五声音阶。
毕达哥拉斯后来创立了一个宗教形式的毕达哥拉斯学派。
这个学派有一些非常奇怪和荒诞的教规,例如要求该派弟子不准碰到白公鸡,不准用手掰开面包而且不能把它吃完,不准在光亮的地方照镜子,不准吃豆子等等,弄得好像遇到白公鸡教主的一身的神功大法就要破功了一样。
东西方人对事物探索的路径可能会不同,但人性终究是一样的。这些教规其实就一个目的:不准冒犯教主毕达哥拉斯的威严,从而不断将其神化,达到保护教主利益的目的。
不过当时有个爱动脑筋却政治觉悟不高的学生希伯索斯,他没能深刻领会教规的深意,只学会了毕达哥拉斯钻研学问的方法,当他细心研究了“毕达哥拉斯定理”(也就是中国说的勾股定理)后,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不能表示为整数比,这个值其实就是根号2。
根号2是个无理数。
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基础理论是“数是万物的本原,事物的性质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,万物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序。”
也就是说毕达哥拉斯眼中,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是:
万物都是数,万物之间的关系都能表示成整数比。
但是这个“死脑筋”的徒弟,竟然发现根号2不能被整除,也就是无法表示为整数比。
这一发现直接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基础,相当于推倒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不久的数学大厦。
于是愤怒的毕达哥拉斯下令把这个爱动脑筋的学生投到海里喂鱼了。这种刑罚在中国古代叫“浸猪笼”。
希伯索斯被投海喂鱼
自此,西方世界再也不敢探索无理数,也就不知道该对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无理数根号2怎么开方了。
直到2000年后,大明王朝的朱公子用自制的81档大算盘算出了这个结果。
朱载堉发明的81档双排大算盘复制品,近3米长。于今沁阳市朱载堉纪念馆
朱公子在家里创建实验室、研发基地,写音乐、舞蹈、地理、历法方面的论文,创作诗歌,编排舞蹈,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乐器,大型计算机……
可以说朱载堉的家就是当时中国的中关村+横店,世界的硅谷+好莱坞。
他最伟大的学术成果“十二平均律”就是在这儿研发出来并写成论文的。
或许天才都是寂寞的。
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当世只有几个人才能看懂;巴赫梵高死了很多年后他们的作品才得到认可。
朱载堉跟这些天才的命运是一样的。他的著作当时没人能看懂,朱载堉每次写完书,他都呈给当皇帝的大侄子,希望能被重视,可得到的结果都是泥牛入海。
直到1596年,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股脑儿写在一起,编成《乐律全书》,包含了天文地理、音乐、数学、计量学、乐器、舞蹈学、诗词等各个品类,万历看到后敷衍的回复了一句:
宣付史馆,以备稽考。
虽然这个皇帝值儿就给了这么一句敷衍的话,但这对朱载堉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凭这一句话,《乐律全书》就有了国家认可的身份,可以名正言顺的保存在国家图书馆,不至于失传或者流落为网文。
此时,朱载堉的父亲已经去世6年,而包含了他一生所有研究成果的《乐律全书》也已出版并收藏于国家图书馆。此时的朱公子没有了一切顾虑,接下来的时间他主要对朝廷做了两件事:
请辞郑王爵位;要求废除不准百姓私自研习历法的法律,并修改当前历法的谬误之处。
1597年初夏的一天,滔滔千里赣江波光粼粼,在万安段险峻的十八滩附近,突发了一起沉船事故。
但见有两个人在水中挣扎着,不多久一个就不幸溺水身亡了。另一个抓住了一块木板,向岸边游来。
这个又一次死里逃生的人就是利玛窦。之后他搭上了另一条船来到了南昌,并在此逗留3年。
在此期间,朱公子与钦天监多次辩论,指出历法的错误,要求改法。《明史》记载了这一过程的惊心动魄,监正张应侯等人多次欲将朱载堉置之死地,此前呼吁改历的多位官员也已被他们或谋害或贬黜了,幸亏朱载堉身份特殊,而且由于他的人品和才华被当时官僚集团喜爱,朱公子才得以险象环生。
不过这一争论引起的风波甚大,万历亲下圣旨平息此事。
那时候朝廷每月都有邸报下发地方政府和各位王公世家,这些邸报相当于《新华日报》,起源于汉朝,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。
而利玛窦在此期间积极参与为历法辩论出主意并撰写了大量文章。后来由他口述,徐光启执笔撰写了天文测量的著作《测量法义》。
利玛窦一定是在此时知道朱载堉的。此后他为了能觐见皇帝,去南京攀附建宁王,并呆了7个月。
建宁王朱多节与郑王世子朱载堉是本家,关系要好,他家中想必有皇家藏书《乐律全书》,而且邸报一应俱全。
利玛窦极有可能读到了利朱载堉的著作,学会了十二平均律,并把它传到了欧洲。
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卓仁祥先生考证了此期间2封利玛窦的书信,两份书信中都提到了朱载堉,以及朱公子对历法的测量结果。
另外,在《利玛窦札记》中也有相关的记载。
自此,十二平均律有幸传到欧洲。
55年后,利玛窦的好朋友马林·梅森终于在著作《宇宙的和谐》中给出了西方世界的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。
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十二平均律被传到西方后,西方学界对此极为重视,并以此为基础改革形成了现代西方音乐理论。
巴赫就是研究十二平均律的集大成者,他融汇贯通了新的律学理论后,鼓励作曲家使用十二平均律作曲,并写下了48首前奏曲与赋格的《Well Tempered Clavier》。
为什么是48首?因为十二平均律有12个半音,每个半音均可构成一个大调和一个关系小调,总共24个调式。
巴赫每个调式写了2首作品,一首前奏曲,一首赋格,所以共有48首。
《Well Tempered Clavier》被翻译成为《平均律钢琴曲集》,其实直译的话,意思是《好的律制键盘》,所以很多人否定了朱载堉对巴赫的影响,说这只是翻译造成的相似,实际与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,朱公子冤枉啊!
其实中国人对朱载堉的误解、冤枉起止是现在,也岂止是一些知乎等平台的作者,从古至今,大到皇帝,小到老百姓对他的无知与误解一直存在。
最严重的要数乾隆。
康熙时期,西方音乐理论已在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发展成熟了,此时又来了几位有名的传教士,其中有南怀仁、汤若望。
康熙对科学和艺术十分感兴趣,他又向这些传教士学习了西方音乐。
朱公子的学说转了一圈,又回来了。
这看上去好像是中国发展朱载堉学说和中国音乐的契机,然而这对朱公子来说又是一次不幸。
这位康熙大帝也是个喜欢在学术上证明自己的主儿,亲自撰写了著作《律吕正义》,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画蛇添足的加了2律,搞了个14律出来。
一个本来正确的理论,非要别出心裁,结果又被他搞歪了。
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,翻出来了朱公子的著作《乐律全书》,呈奏给乾隆。
乾隆这老头自称十全老人,更是个好大喜功的主儿。一看不得了了,这分明是要推翻爷爷康熙大帝的理论呀,于是下令狠批朱载堉以及他的著作,说是胡说八道,甚至爱写打油诗的他亲题了两首御诗来批斗朱载堉以及他的学说。
现实中的纪大烟袋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忠厚,一看皇帝倒朱,一声招呼,翰林们一顿口诛笔伐。
呜呼哀哉,我朱公子。
像不像毕达哥拉斯把学生希伯索斯“浸猪笼”事件,好在朱公子已经驾鹤西游,不然定会给乾隆再一次扔海里。
利玛窦的远征,对朱载堉来说是个幸运,对世界科技和文艺的发展更是个幸运。
没有利玛窦带着坚定的信仰和使命感,为传教苦学汉语,掌握中国文化,朱载堉一生的努力,可能付诸东流。
朱公子的研究成果被带到欧洲后开枝散叶,繁荣发展。
新文化运动后,西方音乐理论又一次以崭新的面目重新返回华夏,终于被我们后人接受。
遗憾的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现代音乐最重要的基础理论,等比数列、无理数论述、开方运算等都是我大明王朝一位“布衣王子”的贡献。
而利玛窦,或许就是那个他一生最重要的知音吧。